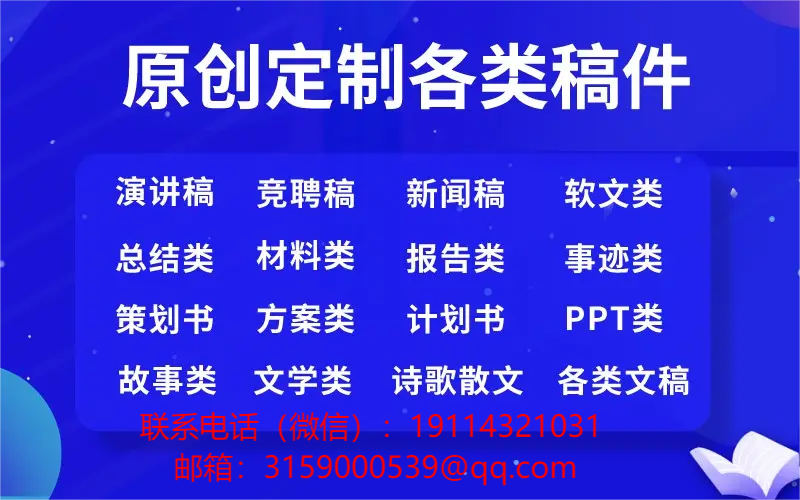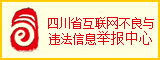作者:孙友军
记得数年前武汉市政协文史委的领导陪同我登黄鹤楼时说的一段佳话:当年黄鹤楼管理办公室发函请毛泽东主席题写“黄鹤楼”三个字。毛主席题写了好几幅寄来供选择。管理办请来书法专家比选,选来选去还是觉得信封上“黄鹤楼管理办收”中“黄鹤楼”三字最好。我们现在看到的挂在黄鹤楼上的“黄鹤楼”三个大字就是信封上的字。这说明一个道理,书法创作的过程,就是书家性灵情感借笔墨抒发的过程。毛泽东书写信封时正是自由的情感与性灵,达到“纵情恣性”的状态时,才写出了展现这种真情至性的上佳之作。这正是最不修饰,运笔随心,精神和平时工力的自然流露。
观毛泽东的诸多作品,都能感觉得到都是乘兴挥洒,用笔灵动潇散、率真随意,融入行草书笔姿,淳朴而寓稚气。其笔墨涩而不滑,流而不飘、留而不滞,率性恣肆,行气贯通、拙巧互用,字法不循常规。就墨色而言,温润自然、火气退尽。“书者如也,如其学、如其才、如其志,定然是其心性的反映。清人刘熙载曾云:“笔性墨情,皆以其人之性情为本。是则理性情者,书之首务也”。
古人“书法”一般情况是基于写字记录的实用层面,今人却为“书法”而“书法”。《兰亭序》实为当时的文化名人群搞了个线下活动,大伙儿作诗编了本《兰亭集》,王羲之为之作序打草稿。这草稿打完觉得不错,但有几个错字。当晚回到家中,重抄三遍,结果再也找不到当时的感觉了,怎么也整不出来了。由此可见,好作品亦是妙手偶得之。
被称作天下第二行书的颜真卿的《祭侄文稿》,更是“草”到不能再“草”的草稿!《祭侄文稿》远溯二王,将古法融入新意,用笔以篆籀圆笔为主,兼施以方笔,展现出一种斩钉截铁的态度,裹锋运笔,打破了字形大小均等、左右对称的常用方法,正面取势,在字形上因字赋形,不刻意而为,参差欹侧,舒朗适宜,使线条更加流畅,有一种浑然天成的韵味。为什么能有这般出神入化的效果呢?颜真卿在书写这篇文章的时候是悲愤交加的,情绪上也是难以控制的,在笔墨之间就没有照顾到工拙的问题,全是感情和精神的自然流露,所以《祭侄文稿》给人的第一感觉就是线条凝重,笔力艰涩,笔势雄奇,笔墨线条全依赖于感情,沉痛悲愤难掩,将笔墨和个人情感有机地高度统一。
而天下第三行书,苏轼的《寒食诗帖》也曾面临王羲之同样的尴尬。苏轼由于政治上的迫害,反对王安石变法,被调离京师,后又历经乌台诗案,不久被贬到黄州,来到黄州的第三年,到寒食节的时候(清明节),苏轼看着自己简陋的房屋,再想想自己被贬不受重视的遭遇,心生感慨,穷途末路,于是提笔写出著名的《黄州寒食诗帖》。此作品是苏轼随手即兴创作,没有正式的落款和印章,如颜真卿《祭侄文稿》一样,都是有感而发的草稿。后黄庭坚看见这书法写得不错,建议苏轼重抄一遍保留,结果可想而知。
所以,为“书法”而“书法”不可能有好“书法”。“故道常无为而不无为”,书法“神作”是自然灵动的“无心插柳”,不是有意为之便可以轻易成就的!这是一种“得意忘形”的自由。这种即兴式的抒怀,来自文人的潇洒快意,是一种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情绪,有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玄妙。徜徉其中,既享受情感宣泄后的快活,也构设了一场内蕴修炼之境。(此文癸卯初秋修改重发于三江熊猫自然保护区避暑山庄)